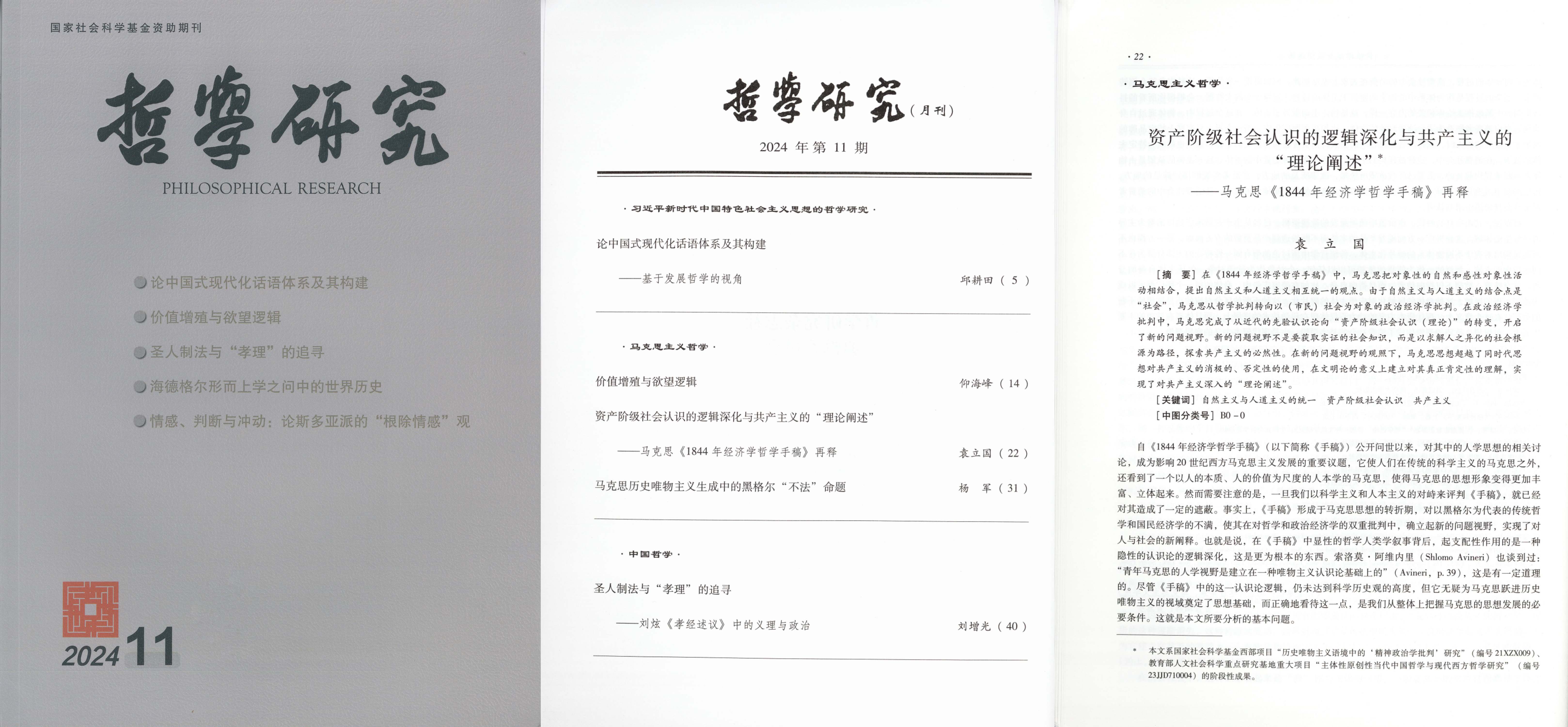
《哲学研究》2024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袁立国,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政治哲学。
文章概要
作为思想经典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形成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转折期。在这部作品中,对以黑格尔代表的传统哲学和国民经济学的双重批判,使马克思确立起新的问题视野,实现了从先验认识论到社会认识论的转变。尽管《手稿》中的这一认识论逻辑,尚未达到科学历史观的高度,但它无疑为马克思跃进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准确地揭示这一点,是我们整体地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必要条件。
首先,马克思在《手稿》中通过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揭示了一种“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而是“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由于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统一的载体是社会,马克思指出,正是在社会生产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以生产为中介,马克思从自然存在论转入社会存在论,把近代的先验认识论转换为对塑造了近代主体性的社会条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进行反思与批判的社会认识论。
其次,马克思的社会认识论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展开的。尽管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采用“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但其目的不再是揭示“国民财富”的一般原理,而是揭示“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之人的生命的感性表现,以此说明经济“运动的联系”。这样,哲学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经济学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全部被批判地揭示为人与世界的异化关系的表现形态。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社会认识论变革,并不是一种“领域转换”,而是应该理解为“逻辑深化”,即一种对认识或知识问题本身的“元批判”:由于意识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在总体性社会进程中,扬弃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设定,对认识问题进行实践的澄明。
最后,马克思的社会认识论并不是对现实社会做置身事外的没有任何偏好的纯然理论的分析,相反,这一分析是基于无产阶级立场进行的,其内在具有实践的指向性:以异化劳动批判论证社会革命的动力,并最终为社会革命的最高愿景——共产主义的必然性——确立现实的起点。在新的问题视野中,马克思以“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为支点,改变以往对共产主义的纯然消极、否定的使用,在文明论意义上揭示了共产主义作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是以在社会层面完成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复归、获得“总体的人”为最终形态的。在此视域中,作为“理论阐述”的共产主义,与作为否定不合理现实世界的“运动”的共产主义,具有内在统一性。在其现实性上,“历史的全部运动”是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是“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具有历史客观性;而历史之所以能够获得这种实现,是由于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这样,共产主义就在主观性与客观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现实性与历史性的辩证统一中,获得了证明。
总之,马克思在通往唯物史观的道路上,固然有不同阶段的思想变化,但这些思想变化往往又是以其认识逻辑的不断深化和内在发展为契机,才得以可能的。对本文而言,对《手稿》进行再释的全部问题的核心,就是要抓住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社会认识方法,再现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的这一关键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