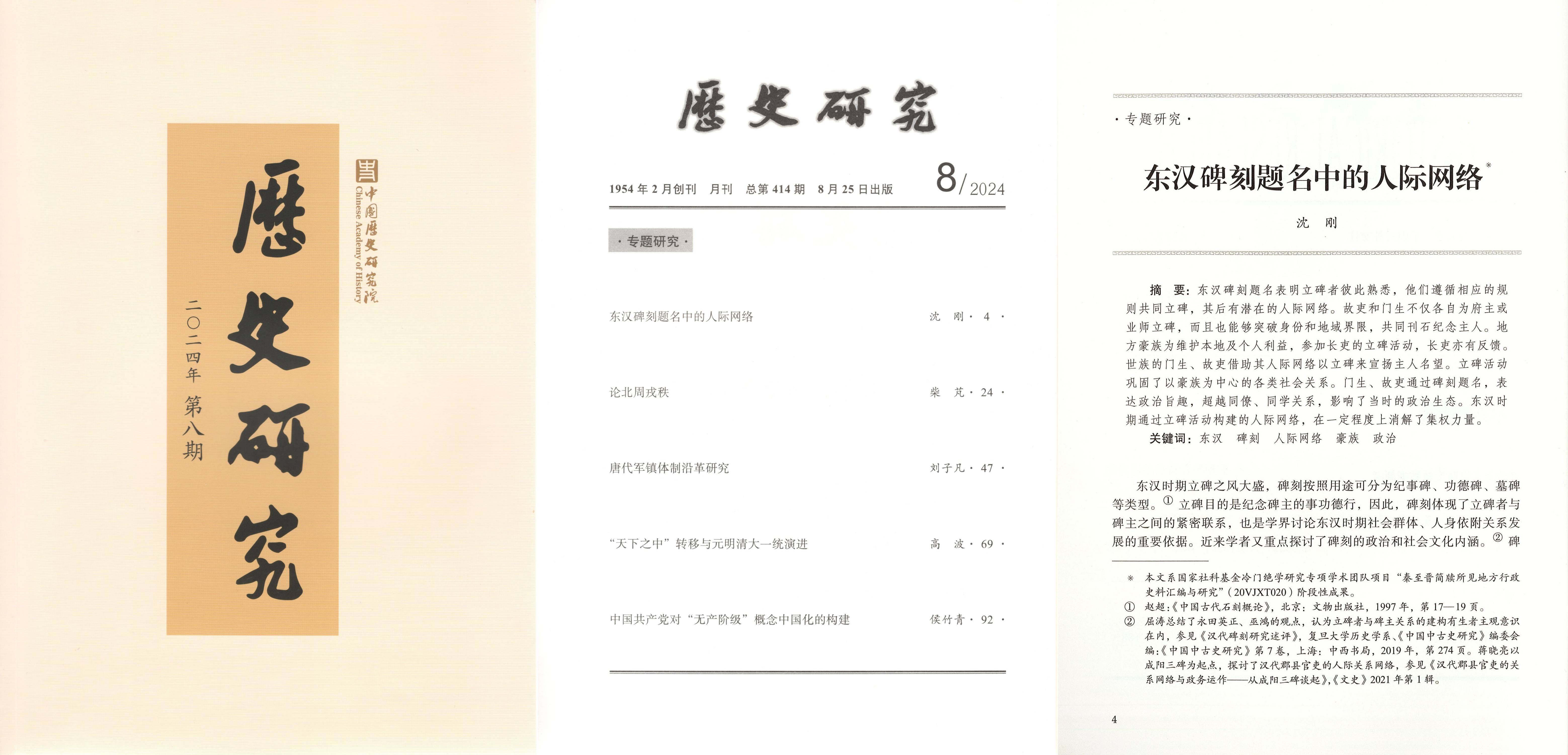
《历史研究》2024年第8期
作者简介

沈刚,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秦汉史、出土文献。
文章概要
东汉立碑者将题名著于碑末。门生、故吏是主要立碑者,他们因无明确的利益纽带与道义上的义务,其人际网络则隐而未彰。本文利用碑刻内容、题名者籍贯、任职地,以及不同碑文的相互联系等信息,佐之传世文献,发掘其中人际网络的发生机制、内部秩序等。
立碑活动是拥有共同理念的一群人,遵循一定的规则,经过协调、运作的有组织行为。整齐、单调的碑刻题名中有潜在的人际网络。故吏立碑是以几位故吏为主,纠合其他故吏共同商议的结果。本地故吏为长吏竖立功德碑或墓碑,皆强调长吏在时任地点的功绩。他们关注本地、重视桑梓,表现出强烈的地域倾向。同地故吏之间有相熟的人际网络。异地故吏则主要为长吏竖立墓碑,他们借此机会展示超越地域界限的人际关系。儒生求学固然是为了研习经学,但交游同好也是目的之一。门生们与业师朝夕相处,意味着门生之间也有深入交往的机会,形成跨地域交结。进入碑刻题名的门生是有意识选择的结果。因有的碑主身兼业师和长吏双重身分,故亦有门生、故吏合作立碑。他们突破各自身份和地域限制,因碑主而结成新的人际网络。
豪族势力在东汉时期进一步扩张,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占据优势,与东汉立碑活动密切相关。地方豪族在立碑场合与地方长吏交结,努力建立起和谐关系。他们参与立碑活动主要是出于维护地方以及自身利益考虑。地方豪强利用长吏祭祀地方神灵、刊石纪念的机会,重拾这些神祇作为地方的精神符号,使其成为连接本地民众的精神纽带,以巩固其在本地的势力。长吏出于地方治理的需要,也支持地方豪族立碑。这与东汉时期地方治理模式变化的整体趋向一致。世族多以碑主身份出现在碑刻中,其题名者多为门生、故吏。这些门生和故吏通过彼此间的人际网络自发组织起来,以石碑为载体,称颂碑主功德,夸赞碑主的祖先世系辽远、出身高贵与家族昌盛,希望世族的声望、事迹传播久远。门生、故吏通过横向联系所构筑的人际网络,帮助世族扩大了声誉。不同层级的豪族在碑刻内容中扮演了不同角色,成为东汉社会群体流传至今的固化记录。回到立碑的历史现场,立碑活动也可视为立碑者主动建立与碑主的联系,积极参与塑造社会规则的一种途径。他们通过集资刊石、颂扬碑主或参与碑主主导的立碑活动,密切了与碑主及立碑人之间的交往,巩固了以各层豪族为核心的社会关系。
门生、故吏以参与立碑为手段,建立起比同僚、同学关系更为密切的联系,对东汉政治产生了一定影响。具有官吏身份且情谊深厚的故吏和门生,形成了故吏—故吏、门生—门生、门生—故吏几类组合,构成联系密切、志同道合的人际网络。这种横向的人际网络投射到东汉官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政治生态。立碑题名反映的是立碑者基于共同政治理念自愿选择的结果,是门生、故吏身份二次组合而成的共同体。由此,立碑活动及铭文显示出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书名于碑这种特殊的方式宣示了一个个以主人为圆心的政治群体;另一方面立碑是政治关系的仪式化表达。一群志同道合的门生、故吏,通过石刻这种载体,永久、醒目地呈现其人际联系。相比于现实、具体的政治活动,他们以共同的政治利益、志趣为出发点,以合法、平和的形式长久地展示其政治交结,甚至政治倾向。东汉勃兴的立碑风尚是当时政治、社会现实的反映。普遍存在的立碑活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治、社会中的集权力量。尽管皇权也做出必要的反应,但制度设计的内在矛盾,以及社会俗尚影响,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直到魏晋时期实行碑禁,导致立碑权力上移,树立石碑不再是门生、故吏以及地方豪族构建人际网络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