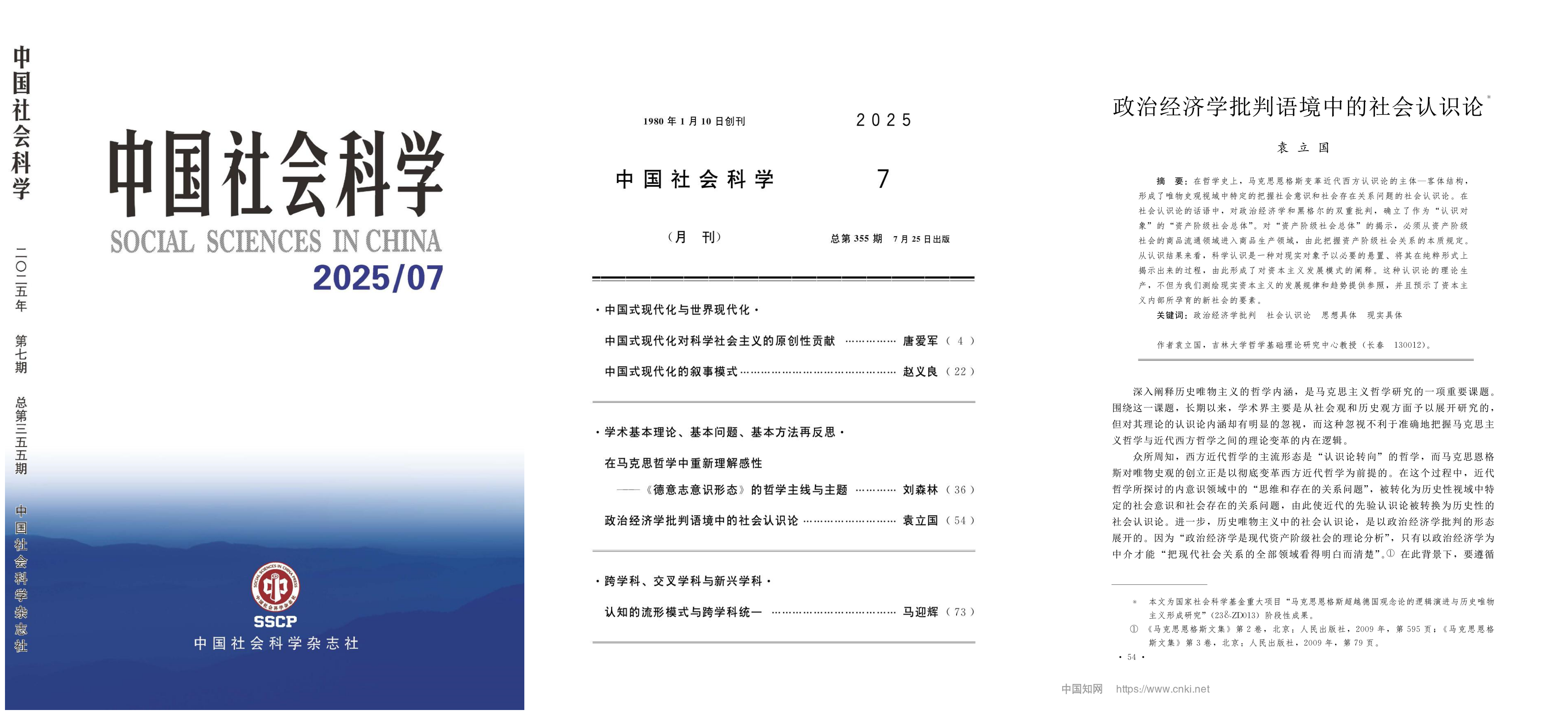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7期
作者简介

袁立国,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
文章概要
在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受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人们往往把认识论视为专属于近代哲学的特定性理论,从而更多地从本体论哲学视角阐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这种解读不仅忽视了马克思哲学的整体性,更大的问题则在于:由于认识论分析的缺失,导致其无法回答马克思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问题。因为马克思正是基于对近代哲学的总体批判才形成科学的历史观,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建构。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不是“放弃”而是“转化”了认识论的旧有形态,即实现了从近代“先验认识论”向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认识论”的转变。基于这一理论背景,本文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分析马克思的认识论革命,呈现其思想的科学性本质。
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诞生中,近代先验认识论被转化为以探讨特定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社会认识论,由此形成了意识形态和科学认识的理论分野。特定的社会意识既可以是对现实的社会存在的真实表达,也可以是对现实存在的虚幻或歪曲的表达。在前一种情况中,它作为客观的社会认识,反映社会矛盾并表达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趋向,是社会认识的科学性自觉;在后一种情况中,社会意识作为现实存在的虚幻的表达,它掩盖社会矛盾并表达反动的观念,这时它就从社会意识沦为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重新摆正了思维和存在、理论和生活之间的合理关系,并且其作为社会认识的科学,还具有指引人类实践以推动社会的自我扬弃和实现总体性的社会革命的诉求。因为一旦组建着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被揭示出来,科学的社会认识就转化为对现实进行积极介入的力量,从而实现“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
马克思基于对黑格尔社会唯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经验论的双重批判,将“认识对象”确立为以现实社会为“实在主体”的“资产阶级社会总体”。正如康德以“先验观念论”和“经验实在论”的统一综合了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马克思以“思想具体”和“现实具体”的否定性统一,使社会认识论既是可知论的,又具有开放性的特征。首先,“思想具体”和“现实具体”的异质性,意味着我们必须把“现实具体”作为认识的源头活水,坚持开放性、历史性的认识态度,避免独断主义。其次,“思想具体”是对“现实具体”的概念式“再现”,而非对其表面关系的“反映”。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前提进行反思,以“抽象-具体”辩证法扬弃了范畴的简单规定,使其上升到具有“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的“思想具体”,超越了经验主义观点。
马克思超越了停留在商品交换领域的意识形态观点,进入到起支配性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分析的视域,体现了从资本主义“表现形式”到“本质关系”理论路径。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不仅流通的过程被证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上的“纯粹的假象”,并且认为生产也须以流通为中介,才能超越“一般生产”,进入价值形式(M-C-M’)主导下的商品生产。所以,把生产作为“实际的起点”和“起支配作用的要素”,这不是从历史关系来谈的,而是以社会结构中各部分的相互作用为着眼点,提出了解析资产阶级社会总体的逻辑起点。只有回到生产关系中,由商品流通所产生的“表现形式”的遮蔽才能被祛除,人们才能就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真实地位进行认识。
由于既定的主体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的“具体总体”的“再现”,并不是与其现实存在的“直接同一”,而始终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但这种差异并不是认识论的缺陷,相反,它表明了在社会认识论的理论生产中,科学认识是一种对现实对象予以必要的悬置、将其在纯粹形式上揭示出来的过程。马克思就此认为,“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而是应该在“思想具体”层面把握资本运动的特征和规律,避免对表面的关系不加辨析地描述。由于资本主义总是自行遮蔽,日常意识根本无法洞穿资本运动的真实过程,因此惟有以认识论的科学抽象,通过假定资本在远离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分析它如何自行其是、自我显现,才能建构起关于资本运动的诸环节的逻辑规定,进而预测其发展方向。正是按照这一方法,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内在地具有走向危机的一般趋势,呈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总之,以历史唯物主义所内蕴的认识论革命为切入点,本文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分析了社会认识论的认识对象、认识路径与认识成果。与西方近代认识论非历史性和非社会性地解答“思存统一性”问题所不同,马克思的社会认识论探讨了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总体”的理论的“再现”之路。在此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社会认识论,根本性地关乎社会主义之科学性的基础,是一项旨在实现社会总体变革的科学理论。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性发展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都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