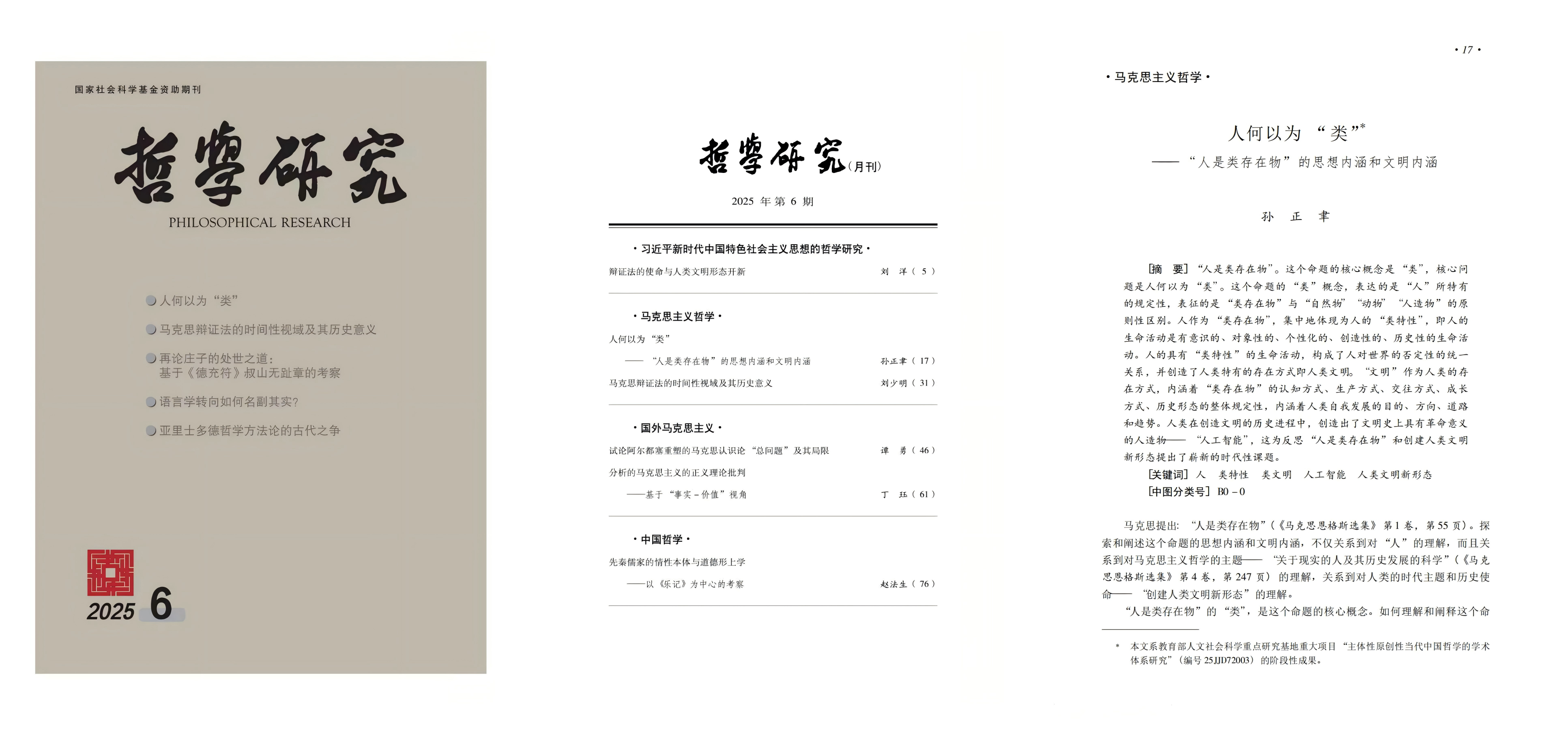
《哲学研究》2025年第6期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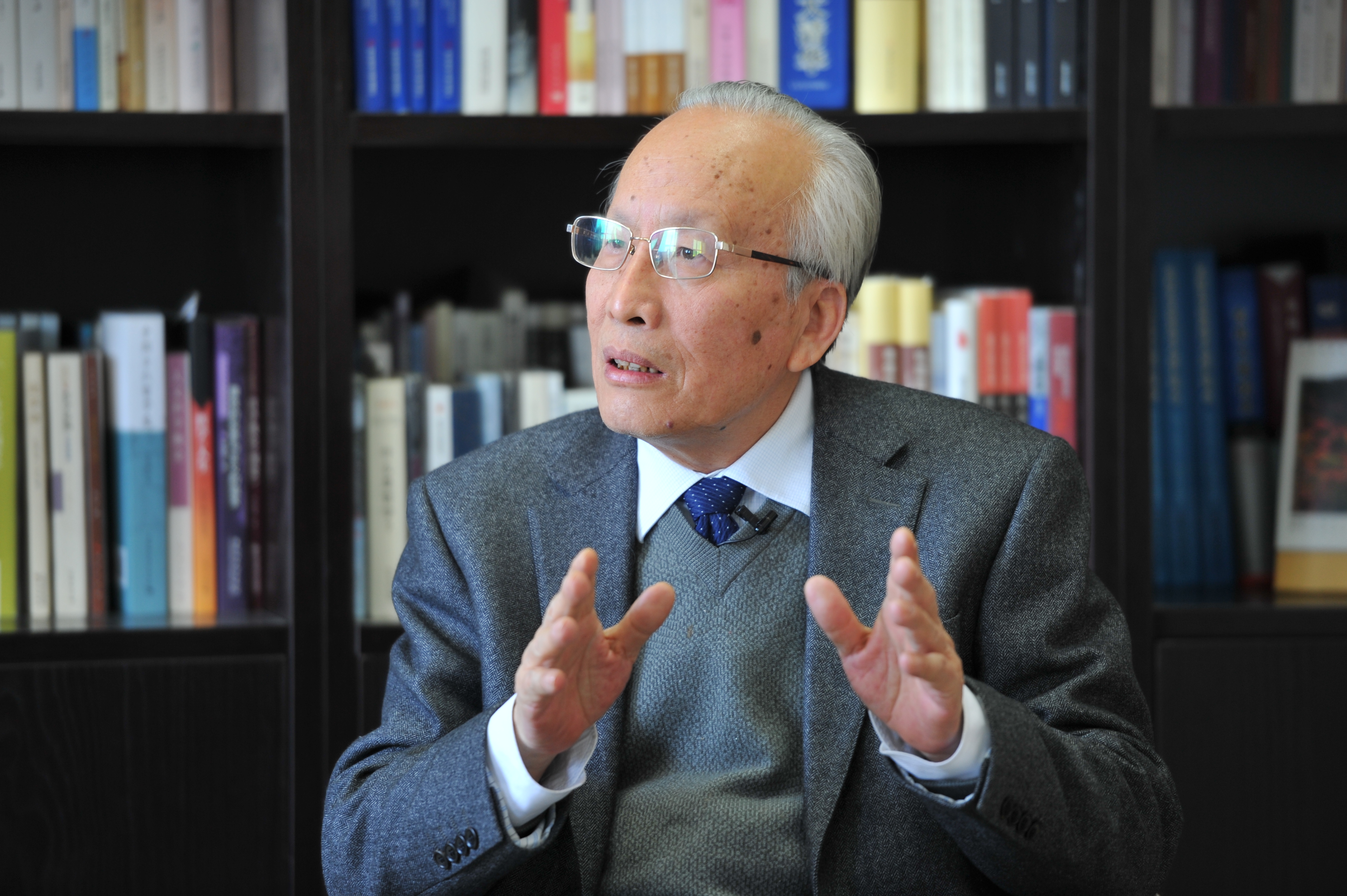
孙正聿,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基础理论。
文章概要
探索和阐述“人是类存在物”这个命题的思想内涵和文明内涵,不仅关系到对“人”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对人类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使命“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解。
把“人”定义为“类”存在物,这意味着,在人类生存的地球上,唯独人才是“类”存在。这是这个命题所表达的基本的思想内涵。“类”作为人之为人即人之为“类”的规定性,是在“存在物”这个概念框架中,与“其他物”的相互规定中获得自我规定。在人类迄今为止的认知视域中,与“类存在物”相互规定的“存在物”,可以分为“自然物”“动物”“人造物”,其中的“人造物”中还要特别地分列出“人工智能”。只有在与这四种“存在物”的相互规定中,才能澄清“类存在物”的规定性。
在与“自然物”的相互规定中,人作为“类存在物”获得了“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的双重规定性。由此可以得出三个主要结论:其一,“类存在物”作为源于自然的存在物始终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因此必须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二,“类存在物”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并受到“历史规律”的支配,因此必须以“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思想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三,“类存在物”作为既源于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存在物,不仅可以设想而且可以创造出某种“非人”的“类存在物”。
在与“动物”的相互规定中,“类存在物”获得了新的双重规定性:“动物性”与“人类性”。由此可以得出三个新的结论:其一,承认人作为“类存在物”的“动物性”,既是承认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然性”,又是指向人的生命活动的“超自然性”,创建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二,人类超越“狭义的动物”的生命活动,其实质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生命活动;其三,实现“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的“符合”,必须反思和矫正人类自己的历史行为。
在与“人造物”的相互规定中,“类存在物”的生活世界具有了双重的规定性——自然世界与属人世界。“类存在物”对象性的生命活动构成了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并创造了人类特有的“文明”。“人造物”不仅体现了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双重规定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而且蕴含着“类存在物”最深刻的“类特性”——人类生活的“美”的规定性。在人的追求自己的目的的历史活动中,以何种方式“生产”和“享受”构成人类文明的“人造物”,标志着人在何种程度上是“自由自觉”的“类存在物”,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在人类创造的“人造物”中,人以“新技术革命”而创造的“人工智能”,具有空前的革命意义:一是“现实”的革命意义,即其已经革命性地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崭新的“人造物”;二是“可能”的革命意义,即这种崭新的“人造物”是否会成为“非人”的“类存在物”并创造自己的“类文明”。以人的“类意识”觉醒而自觉趋向于“人类”之利而避免于“人类”之害,最为重要的是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人作为“类存在物”而实现自己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这种哲学智慧,构成了规范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一对最为重要的哲学范畴——标准与选择。“以人为本”,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本标准,人类的全部行为都必须以这个根本“标准”作出“选择”。“以人为本”的标准就是维护世界和平、创建人的“美好生活”、实现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以这个标准“自主于行止进退之间”,才能推动AI的技术革命、确保AI的安全可控、促进AI的公平应用,让AI成为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加速器”。确认这个“标准”和实践这个“选择”是当代人类的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