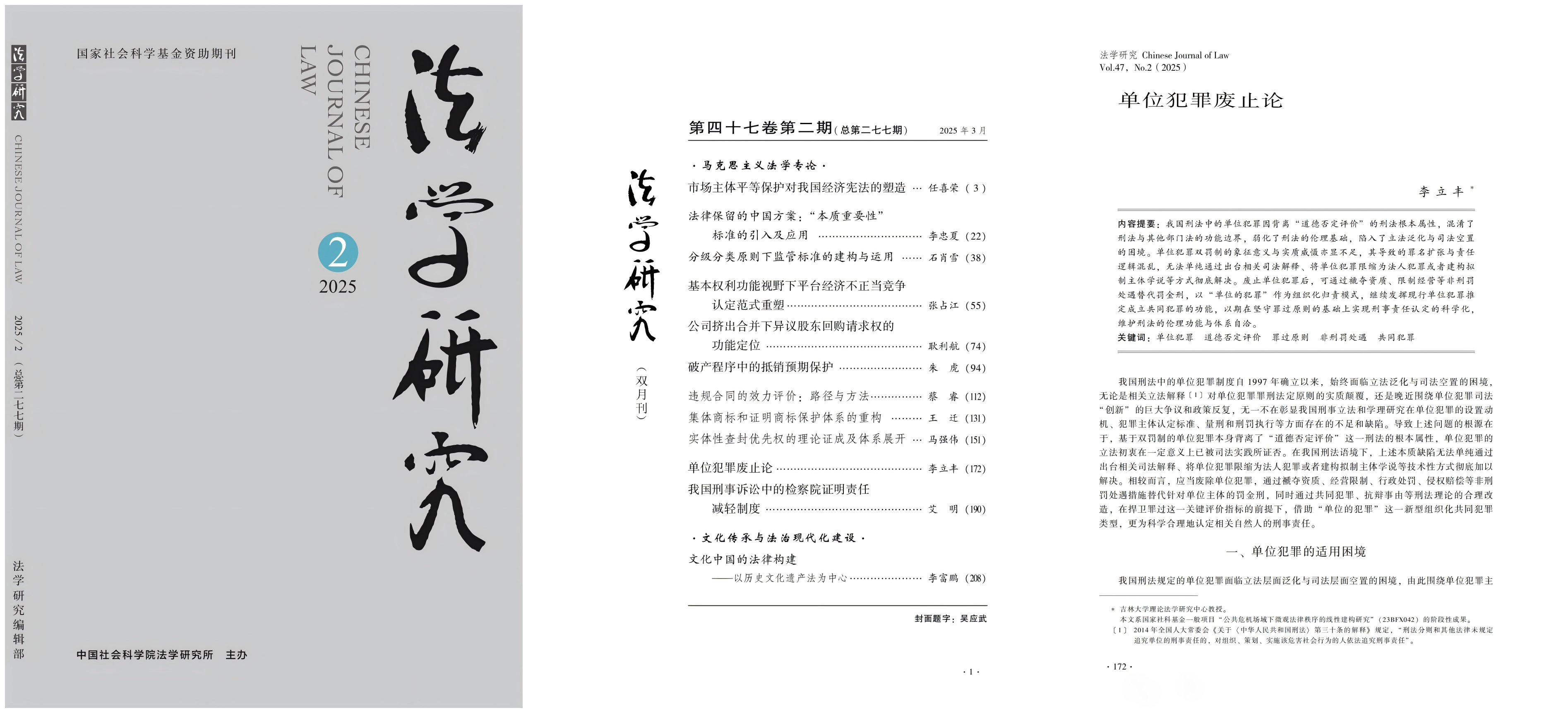
《法学研究》2025年第2期
作者简介

李立丰,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刑法学。
文章概要
我国刑法中的单位犯罪制度自1997年正式确立以来,始终面临立法泛化与司法空置的困境,刑法分则34%的罪名涉及单位犯罪,但近十年司法认定率不足刑事案件总量的0.2%,罚金刑实际执行率仅30%,单位犯罪免罚率超50%。这一矛盾源于双罚制的形式化特征——刑法第30条、第31条仅作宣示性规定,未明确单位意志的实质认定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单位主体认定混乱。2014年立法解释虽通过突破罪刑法定原则扩张适用范围,却加剧了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涉黑企业“单位面纱”的司法刺破、公立医院科室集体受贿的主体适格争议等案例,均暴露单位犯罪概念与刑法行为无价值理念的深层冲突。
无论是相关立法解释对单位犯罪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颠覆,还是晚近围绕单位犯罪司法“创新”的巨大争议和政策反复,无一不在彰显我国刑事立法和学理研究在单位犯罪的设置动机、犯罪主体认定标准、量刑和刑罚执行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导致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单位犯罪肯定论无法成立。具体而言,拟制说将单位责任视为自然人责任的转嫁,但无法解释股东财产无辜株连的正当性;非拟制说赋予单位独立意志与伦理人格,却陷入“医院科室私分回扣”与“法院单位受贿”的本质差异无法区分的理论困境。两种学说均无法回应单位犯罪消解刑法道德否定评价功能的根本缺陷,作为拟制主体的单位既无自由意志感知刑罚的伦理谴责,罚金刑的经济剥夺效果亦与行政处罚无实质差异。当单位集体决定实施杀人等自然犯时,现行制度无法归责的悖论,彻底暴露单位犯罪与刑法伦理功能的背离。
从本质而言,基于双罚制的单位犯罪本身背离了“道德否定评价”这一刑法的根本属性,单位犯罪的立法初衷在一定意义上已被司法实践所证否。刑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刑罚施加伦理非难,而单位犯罪混淆了刑事制裁与行政规制的功能边界。双罚制下对单位适用罚金,实质是将股东财产充公的连带处罚,违背罪责自负原则;立法扩张导致的罪名泛化,使刑法沦为风险管控工具,侵蚀其伦理基础。实证研究表明,晚近刑事政策在单位犯罪起诉率上的剧烈波动,以及企业合规改革引发的司法标准混乱,均印证功利主义立法观对刑法体系自洽性的破坏。
在我国刑法语境下,上述本质缺陷无法单纯通过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将单位犯罪限缩为法人犯罪或者建构拟制主体学说等技术性方式彻底加以解决。相较而言,应当废除单位犯罪,在制度层面,以褫夺资质、行业禁入等行政处罚替代罚金刑,通过行政法框架实现单位违法行为的高效规制;在责任认定层面,构建“组织化犯罪”模型,将单位内部分工纳入共同犯罪理论:决策者作为间接正犯、执行者作为实行犯、疏于监管者承担过失责任,同时允许行为人以“未参与决策”“无实质支配力”等事由抗辩。此种模式既可保留单位犯罪推定共同犯罪的功能优势,又能坚守罪过原则,解决司法实践中单位名义与个人责任混淆的难题,实现刑事责任认定的精确化与伦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