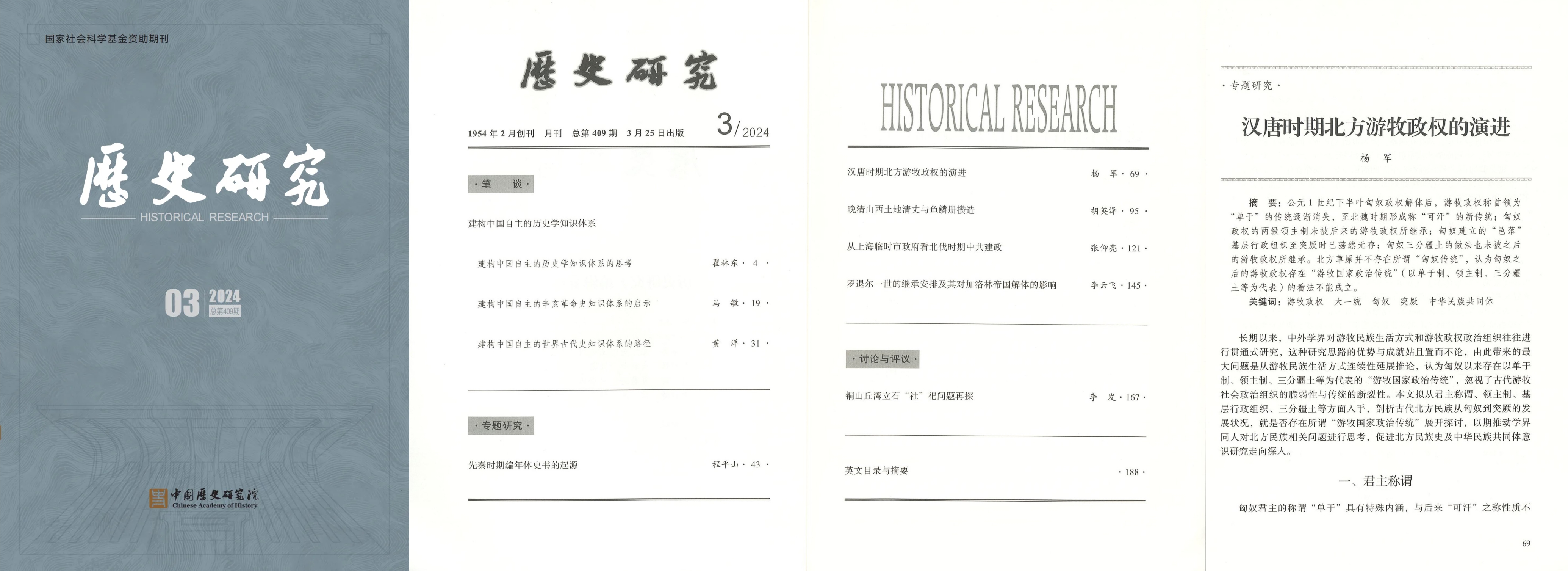
《历史研究》2024年第3期
作者简介

杨军,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辽金史、民族史。
文章概要
汉唐时期北方游牧政权的社会政治组织具有脆弱性,其传统亦存在断裂性。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从匈奴到突厥从君主称谓、政权组织形式、基层行政组织到疆土分配均不存在所谓的“匈奴传统”。
匈奴君主的称谓“单于”具有特殊内涵,与 “可汗”之称性质不同。匈奴统治者所用尊号体现其将西汉王朝与匈奴政权视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与汉朝统治者同样拥有对此政治共同体的主权。随着匈奴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变化,单于称谓逐渐贬值。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匈奴政权解体后,游牧政权称首领为“单于”的传统逐渐消失,至北魏时期形成称“可汗”的新传统,为柔然、突厥等所继承;匈奴政权实行两级领主制,大小领主各有“分地”、私兵,并以单于近亲身分的大领主统领被征服部族,属于部落型领主制。在匈奴政权解体后,这一体制未被之后的游牧政权所继承,檀石槐曾尝试重构匈奴的两级领主制,最终以失败告终,拓跋鲜卑虽在早期曾有重建匈奴领主制的努力,但最终走向建构中原式政权的道路。柔然始终未曾设想构建匈奴的领主制,突厥的领主制则与匈奴迥然相异;匈奴政权最基层的行政组织“邑落”,是在编组基层游牧社会组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匈奴政权瓦解后,游牧社会组织经历深刻演变,至突厥时,最基层行政组织已具有宗族组织性质,匈奴传统“邑落”组织荡然无存;匈奴三分疆土的做法同样也未被之后的游牧政权所继承,檀石槐和拓跋鲜卑对匈奴三分疆土传统的继承,仅仅是形式上模仿,其内涵已发生实质性变化,柔然则直接抛弃匈奴三分疆土的传统,将疆土分为东西两部分,突厥的疆土分割方式与匈奴、鲜卑三分疆土性质则完全不同。由此可知,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政权并不存在所谓“匈奴传统”,在“匈奴传统”基础上构建所谓“游牧国家政治传统”(以单于制、领主制、三分疆土等为代表)的看法不能成立。
匈奴政权解体之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历史进程表现出两种趋势。一方面是民族杂居越来越普遍。由匈奴时代的诸族各有居住区,发展为檀石槐时代的各族交叉杂居,再到拓跋鲜卑早期各族杂居并通婚,至柔然兴起时,已是各族杂糅组成部落。另一方面是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越来越强。由匈奴与汉王朝的对抗,发展至南匈奴附汉,至檀石槐尝试恢复游牧政权时,不得不思考如何切断鲜卑诸部附汉的趋势,之后拓跋鲜卑则放弃构建游牧政权,转向中原发展,最终到柔然时,已自我定位为中原传统模式的王朝。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中华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深刻体现着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特征。
此后草原民族政权建构过程中,皆必须克服两种困境。一是民族杂居普遍化及其导致的难以在游牧社会组织之上建构政治组织;二是即使建构起草原政权的政权组织,其与游牧社会组织的结合部仍旧是草原政权最薄弱的环节。为克服前一种困境,必须树立超越草原诸部的政权认同,在东亚历史格局中,只能是对“中国”的认同;为克服后一种困境,必须建构与中原政权和平交往的机制。由此可见,草原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越来越强,是草原民族自身政治组织演进的内在要求,草原诸族与中原诸族熔铸为更大的共同体,是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