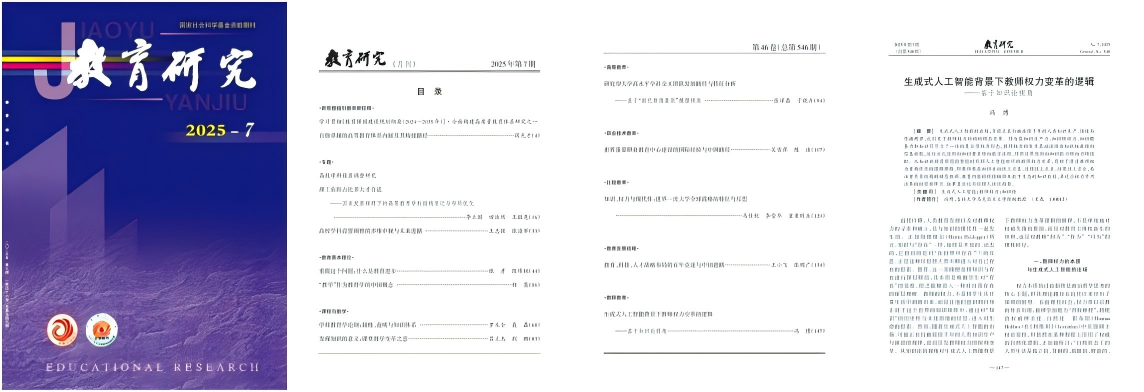
《教育研究》2025年第7期
作者简介

冯博,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文章概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场,可能正在打破延续千年的人类知识生产、演进与传播规律,也引发了教师权力结构的深层变革。近代以来,人类教育发展以及对教师权力的寻求和确立,是与知识的现代性一起发生的。教育的本质是唤醒学生对“存在”的觉察,使之能够进入对自我存在的深层理解。教师的权力,不是将学生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而是让他们意识到自身正处于这个世界的知识矩阵中,通过对知识的历史性与文化语境的反思,进入对生命的思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使这种知识网络出现了新的形态,推动教育权力体系的整体转型,并使教师必须重新面对自身何为、作为与可为的问题。本文立足于知识论视角,围绕教师权力的本质、发生基础、运行方式与作用边界四个方面,系统分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师权力变革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厘清教师权力重构优化的逻辑理路。
教师权力的本质正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场中发生深刻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语言的再组织与语义的重构,使知识的生成逻辑由稳定走向流动,由稀缺走向泛在,促使教师权力不再建立于对系统化知识的占有之上,而是体现为对教育意义的持续生成与价值整合。教师不只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教育中知识选择、话语组织与内容建构的参与者,是集知识生产力、知识规训力、知识服务力和知识引导力于一体的复合型权力存在。技术对教育语境的重塑,促使教师从过去强调内容控制的角色,转向强调意义建构与教育价值引领的新角色。教师对知识的界定、重组和排序,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习路径,也深刻介入社会的知识图谱与价值判断。在新的知识生成机制中,教师不再是简单的知识通道,而是知识解释与意义组织的核心枢纽。面对技术介入后的教育场域,教师的角色从知识的单向建构者转向意义协商者与共创合作者,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也从制度规定走向知识逻辑与教育价值的多重支撑,呈现出从控制性权力向生成性权力的深刻转化。
教师权力发生基础的重构源于从知识权威转向信息祛魅。在前智能时代,教师权力主要建立于稀缺知识的占有、制度的合法性规定以及文化象征秩序的延续基础之上,具有显著的认知权威性与制度正当性。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使知识生成机制由主体主导转向算法驱动,其生成内容具有非意向性、非否思性与非完整性,缺乏对意义、价值与目标的内在关切,挑战了教师传统知识权威的正当性来源。在这一语境下,教师需通过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识别、判断与筛选,重建教育中的价值导向与意义框架。信息祛魅意味着教师不再依靠知识的神秘化,而是要通过清晰而理性的教学设计、对算法偏误的洞察以及对学生发展的关注来确立其专业权威。这一重构过程体现为三个维度:求善,通过确立向善的教育目标,引导知识价值方向;求真,通过批判性理解与反思性教学回应技术逻辑的局限;求全,通过知识系统建构弥补人工智能输出的碎片化与非结构化倾向。教师正是在这一信息祛魅与价值重塑中确立其不可替代的专业地位,在教育生态中持续发挥其方向引领与意义建构的重要作用。
教师权力运行方式的转换表现为从知识势差转向数字流转。前智能时代,教师依靠对知识供需关系的掌控,通过内容传递与节奏调控构建起基于知识势差的引导性结构,使学生在认知依赖中完成学习路径的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改变了这一结构,知识的可及性大幅提升,教学任务的外包性增强,传统的势差机制难以维系。教师的权力运行开始向数字化生态中的动态协同转型,不再依靠对知识的单向控制,而是依靠对多元行动者之间关系张力的调节、对教育内容价值逻辑的组织以及对生成式内容的意义加工。教师需在教学中合理配置技术与学生的交互关系,通过筛选与重组技术生成内容,实现教育目标的嵌入与价值导向的确立。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教学参与者之一,其生成内容需由教师赋予教育意义并纳入教学目标体系。教师在教学组织中构建以创作共同体为核心的协同机制,从而避免因技术主导而引发的教学错位、越位或缺位,确保教育目标与教学路径的有机统一。在教学治理的动态系统中,教师的作用已由权威型主导转变为协同型调节,运行逻辑则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线性走向网络,从静态走向流动。
教师权力作用边界的调适是从知识张力走向力场适配的过程。前智能时代,教师权力的作用边界依赖于基于知识张力所建构的教学时空与语言秩序,通过固定的课堂结构与制度逻辑确立稳定的行为规范与权力边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使教育场域呈现出矩阵化、流动性特征,教师的在场形式与作用方式发生转变,其边界不再由固定的物理空间界定,而是在算法逻辑、语言生成、内容协同中被动态建构。教师需以嵌入者的身份在物理时空与数字场域中展开教育实践,并通过统合宏大话语与个体经验实现叙事结构的复合化,满足教育整体性与个体差异性的双重要求。力场适配不仅是教学空间的调节,更是教学语言、教学逻辑与教学价值的重组过程。在伦理层面,教师需抵抗技术对学生主体性的遮蔽风险,维护教育的非技术化空间,使学生在价值引导与情感支持中保持自由与尊严,从而推动教师权力从静态边界走向动态力场的适配转型。教师不仅要在技术生成内容中嵌入教育目标,还需通过人技协作实现教学节奏的重新调节与边界控制,确立教育场景中教师不可或缺的嵌入者角色。
总之,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刻改变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逻辑,使教师权力的发生基础、运行方式和作用边界都在重构。教师只有在知识方向性上求善、过程性上求真、结果性上求全,通过关系结构的动态协调、教育内容的价值编排及数字生态的知识共创,才能实现权力结构的优化,推动教育主体性与技术进步的协同发展。教师需要持续探索自身的何为、作为和可为,回应权力嬗变的逻辑与可能性空间,实现教育与技术之间的平衡,使教育成为意义生成与价值引领的场域,这不仅是教师权力优化的现实需求,也是数字时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